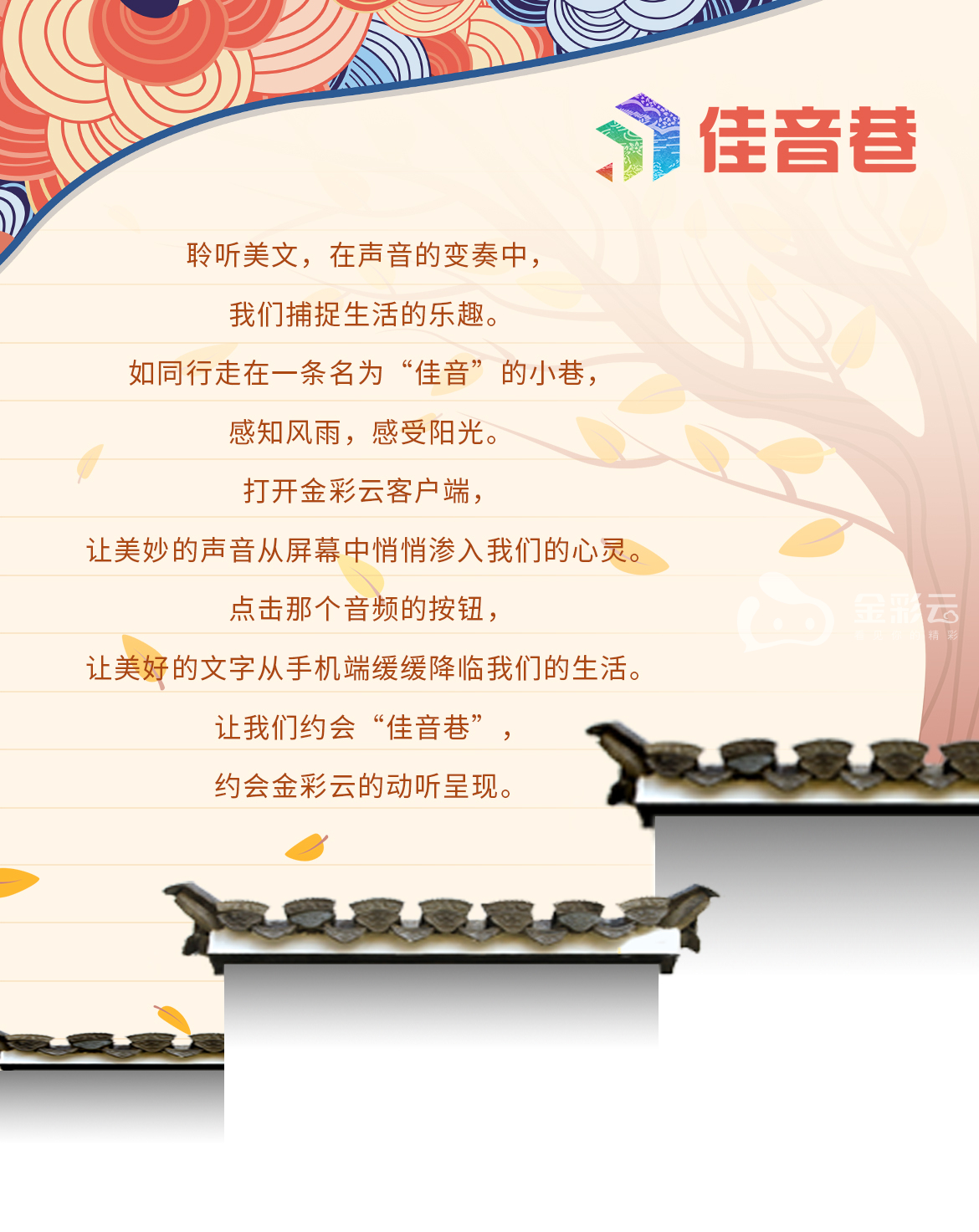
西溪的故事
作者:杨方 朗读者:王雅萱
我若不来,西溪便无故事。我来了,西溪的故事,在我笔下生花。
我与西溪的相会,是一场人与山水的相会。山在那里,水在那里,山水若睡若醒,懵懵懂懂。西溪的山水有时候会在自己的时间里发呆,浑然相忘之时,西溪会呈现出瞬间的静止,那是所有来西溪的人一起做的一个梦。
第一次走进西溪影视基地,风吹来,是梦的气息。影视基地里林木高大,有一种太古之感。临水的建筑,破旧但不破败。走过一座倒影水中的小木桥,进入视线的是光线半蒙半昧的枫树林,林中正拍电影,有钱人家的少奶奶,坐着轿子经过枫树林,遇见劫路土匪,土匪黑衣,蒙面,手持亮晃晃的刀。枫树林因了这些蒙面人的黑衣和道具刀的寒气而气氛凛冽。时气候已是冬天,枫叶一半掉落在地,一半在高枝上被冷风吹得瑟瑟。少奶奶身穿无袖的丝绸旗袍,裸露在外的部分也是瑟瑟的颜色。化妆人员不时拿了粉往少奶奶脸上胳膊上扑,我感叹当少奶奶不易,大冷天拍反季节的戏,如同要求水果反季节成熟。我也感叹原来电影里看见的白胳膊白腿其实是扑了许多粉的效果。
那日电影拍了小半天,我也看了小半天。结束时众人散去,我也跟着散去。出了枫树林,抬头看见青的天,绿的树,淡远的云,墙壁上的阳光,以为自己刚才撞见了一个梦,一个半古半今的梦,一个半真实半不真实的梦。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,也许是因为枫树林里的光线,也许是因为西溪的地气,那梦如同一团氤氲之气,触手可及。它的高大树木,流过青草地的流水,有虚幻倒影的木桥,带着回音的鸟鸣,树枝间布局清晰的蛛网,在我回望的时候,都是透明的。带着灵气和仙气,萧然出尘。
来西溪的人,大多是来寻梦的,影视梦,明星梦。如同寻找桃花源的南阳刘子骥,寻而不得,念念不忘。我毫无目地的来,无意中撞见了西溪的梦。撞见了西溪的梦,也是念念不忘。既出,处处志之,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还能找到那条进入梦境的路径。
我想起一幅画,修拉的油画《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》。画中人物没有动作,只有块面组成的剪影似的形体,分不出五官细节,更没用性格特征。画中人物在各自的位置上形成一种超越时空的凝重,那是一种仿佛不能打破的某种寂静。就像西溪那片冬日萧瑟的枫树林,当演员与现代摄影机器纷纷离开,围观者离开,枫树林顿然陷入万籁俱寂,只剩下渺茫与杳冥相对。它刚才上演了什么?华彩的轿子,白脸白胳膊的少奶奶,黑衣蒙面人,刀。他们出现在此处,又消失在此处,就像被抹去一样了无踪迹。他们是否和我一样,进入了西溪的梦,然后,又破梦而出?
每每想到那片枫树林,我所能想到的便是枫树林里那些拍电影的人。西溪影视基地差不多每天都有电影在拍,清朝的,明代的,宋代的,隋唐的,比隋唐更久远的三国甚或春秋的故事,你方唱罢我登场。小小的一片山水,集中了漫长的时间和天下所有故事。可以说,西溪的喧闹被流水般的人带走。西溪的寂寥被留下。西溪的小,实则大过世上一切山水。
我后来又多次返回过那片枫树林,在不同的时间,在不同的季节,和不同的人。
有时是自己一个人。西溪的枫树林,有一种寂寥的仙意,适合一个人走。渺小低矮的人,在高大的枫树林里移动,像一只紧贴地面的甲壳虫。枫树林仿佛叠印着多重空间。光的,影的,时间的,色彩的。如果留心感受,会有一种错觉,枫树林外还有枫树林。人的枫树林里走,怎样都找不到梦境的出口。寻梦人一直是在梦里走,如同看画人,一直在画里走。绕过一棵大树,迎面又一棵大树,没有风,叶子以静止的状态飘落。枫树的叶子最适合障目,使人看不见天外天,但听得见流水之外有流水。不得不说,小小的西溪,世界虚妄里的无限实在是令人惊奇的,无始无终循环往复的时间,实在是令人惊奇的。光在枫树林里的折叠,实在是令人惊奇的。这一次来是这样,下一次来还是这样。以后来,也还是这样。
有很多次,我与人说起西溪。听的人不以为然,听的人眼里,那不过是一个拍摄电影的地方。有一些亭台楼阁,一些参天古木,一些自然状态的流水,还有木桥,石子路,水井,月出东墙,是一些适合拍古装电影的道具,仅此而已。至于梦,他们的眼睛看不见。梦应该是睡眠状态下才有的,而我,在醒着的状态下看见了西溪的梦。不管别人信不信,我都相信,西溪在西溪的枫树林里。西溪在西溪久远的梦里。它的山水是形而上的。是菊在此,南山在彼,人在世外或梦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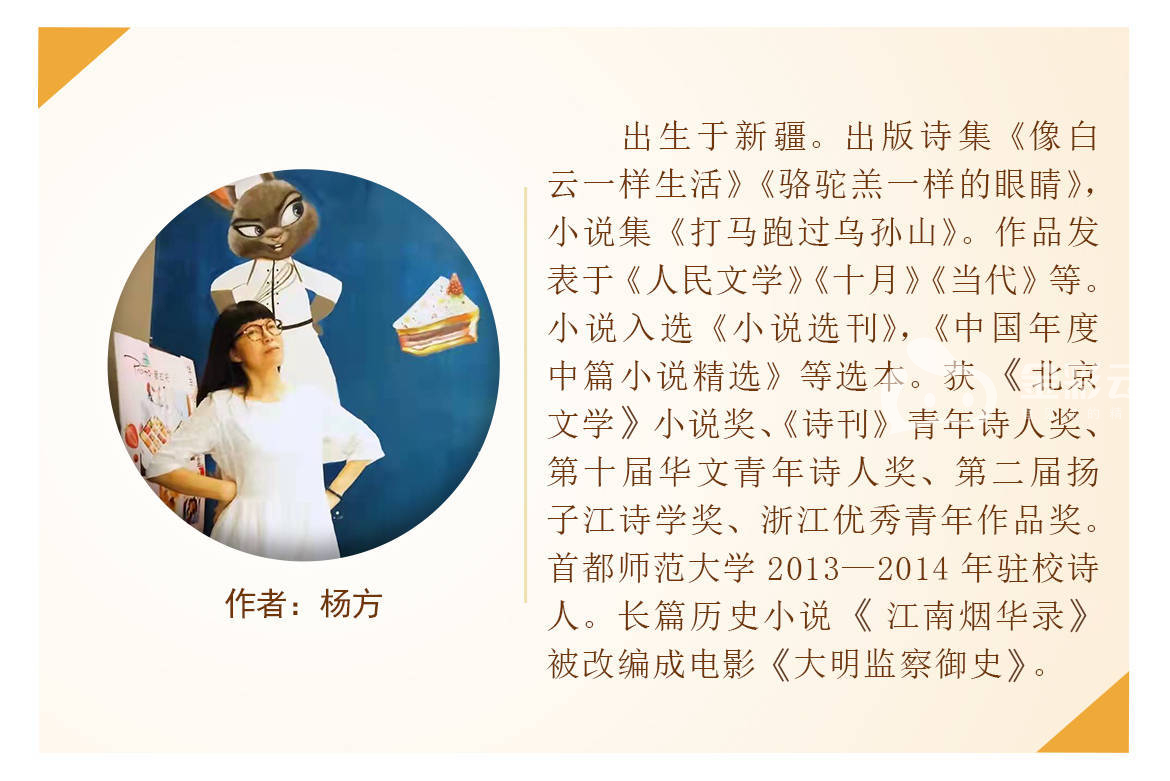








精彩评论( 0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