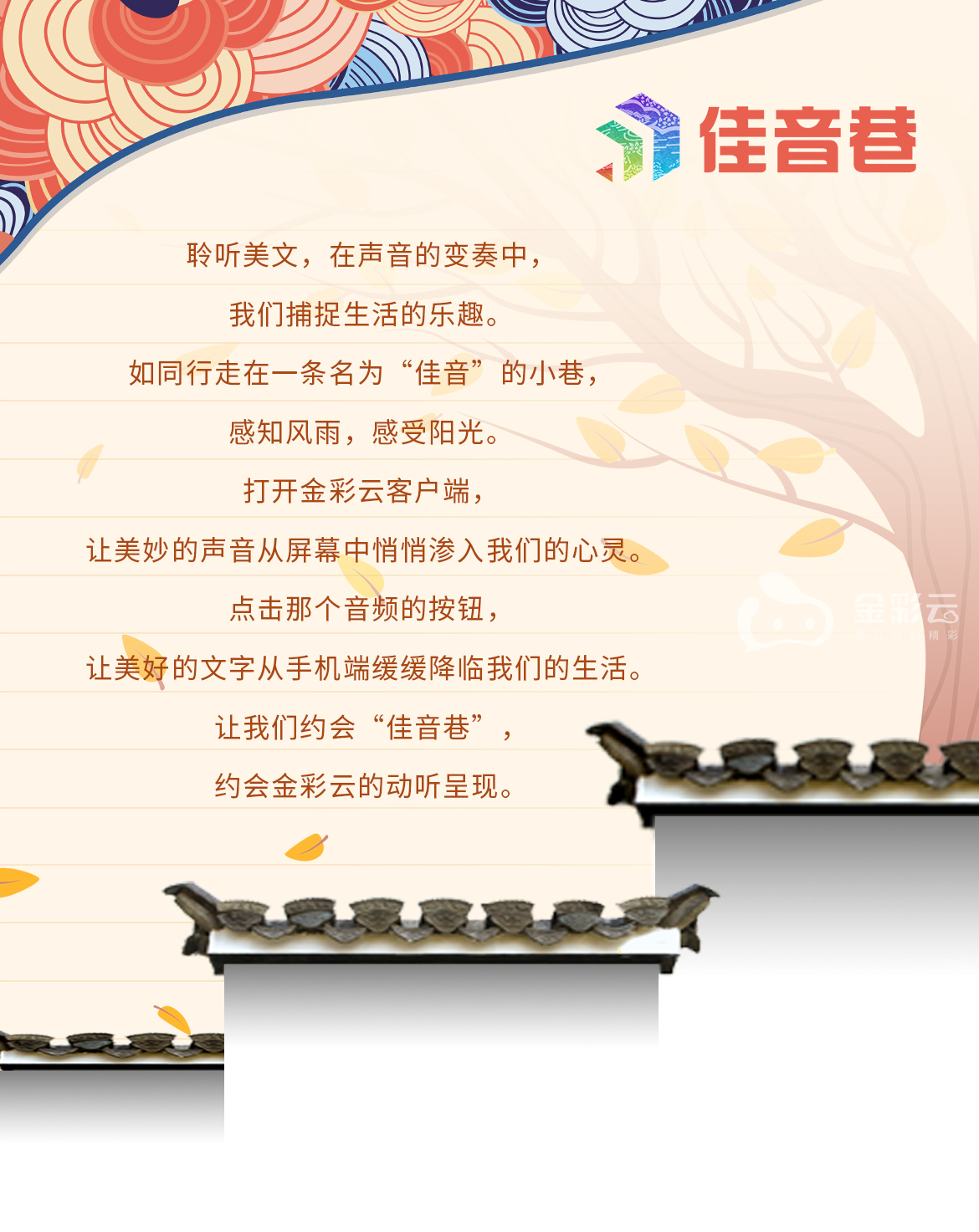
虎娃
作者:伊有喜 朗读者:陈玲
我们称蚂蚁为“虎娃”。为什么叫“虎娃”?有这样疑问的也不是我一个,看蒋风先生的文章,原来蒋风也曾困惑过。从形状上看,蚂蚁与老虎相去甚远,哪怕再大个的蚂蚁,估计也入不了老虎的法眼。蒋风推测说,可能蚂蚁雄赳赳气昂昂奔走的姿态接近于老虎吧。蒋风不是汤溪人,看来,把蚂蚁称作“虎娃”的,也不仅仅限于我们汤溪人。
很多年了,我肯定想不起第一次接触蚂蚁的时间了,但地点肯定是家门口,可能是坐在门槛上吧,可能有饭粒掉落,可能在母鸡把饭粒啄去之前,在幼童偶然的一瞥中,看到从容奔跑的黑蚂蚁,不,我看到了“虎娃”——此后,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迷恋上这种小虫子,除了黑蚂蚁,还有暗红的小蚂蚁,形体更小。常常,我用拍死的苍蝇、残剩的饭粒拦住蚂蚁的去路,让它停顿、迟疑,触触碰碰,让它通风报信,去搬救兵。
虎娃,虎娃——
千张豆腐买来罢。
酒——肉——你——自——买。
在稚声稚气的童谣声中,虎娃们排着长队浩浩荡荡地来了。
千张豆腐是常见的,每天都有上门转悠的豆腐担,卖豆腐的总在固定的时间出现,她每次就停在我家门口的空地上。我们通常用黄豆去换——黄豆是经我择过的,不拘什么豆,总有残破虫蛀的,也有小石子或者小黄泥混在里面,我要把它们统统挑出来,我的眼睛又黑又亮,豆子从一个碗换到另一个碗,这事我做得又快又好。我们拿这些豆子去换豆腐、豆腐干和千张。
豆腐干炒着吃,我的爷爷和父亲最爱用它下酒,那时,我的母亲还在镬孔镬头上忙乎,他俩就喝开了——我对这点很有看法,那么小我就觉得这不公平,但我的母亲只是笑笑,毫无怨言——酒是家酿的冬水酒或者是严州府的五加皮,有时我也去村中小店给他们打点黄酒,经过志清家、金红家,从店里返回,总有人逗我:看看瓶底,漏了。我抱着酒瓶,低下头看看,又抬头看看那个人,朝他恶狠狠瞪一眼——他突然就乐了。据说,有孩童闻言真的会一直低头看瓶底,以致把瓶子翻过来看——结果把酒或者酱油倒掉了。
为什么替人家买千张豆腐?为什么酒和肉要让对方自己买?幼稚的我,哪里会想这些无聊的事。那时吸引我的东西实在太多,光光我家门口就有无穷无尽的新鲜事物。白天飞的蜻蜓、蝴蝶、燕子,黄昏纷飞的老鼠蝙翼,夜里游动的火萤虫、扑火的飞蛾、以及遍地的虫鸣。蜻蜓有双双抱着飞的,有单只悬浮在空中的,但想捉住它们是痴心妄想。门口的泡桐树、树下的大石头。葡萄藤和紫苏,稍远处钻出地面的小草。靠近明堂坑有着蚯蚓屎的地面,弄把小锄头掘起来,就可以掘出鸡鸭非常喜欢的蚯蚓。右侧志清家废弃的菜园,低矮的墙头有缠绕的薜荔藤,它结的果子可以做晶晶亮的凉粉。园子里有高高的苎麻,叶面是青的,叶背是白的,到了秋天,人们就砍了它,剥它的皮,水煮,做成细麻线。而吸引我的是剥了皮废弃不用的麻秆,白白的,中间是空的。我有时用它做木匠钻,有时用它接引蚂蚁上来,上下颠倒,小小蚂蚁不明就里,它就来回不断地匀速爬啊爬。这样的游戏让游戏者有一种上帝,不,老天爷的感觉,高高在上,生杀予夺;有时你又无端感慨做蚂蚁的卑微、渺小。蚂蚁蚂蚁,不,是虎娃——
虎娃,虎娃——
千张豆腐买来罢,
酒肉你自买。
大伯背秤具,小伯饲虎娃。
大伯小伯,我都没有,但志清志有的爸爸是聋子,我们叫做“聋伯”,聋伯的哥哥、志高志芳的爸爸也是聋子,我们叫做“大聋伯”。他们住在一幢很高的有天井的徽派房子里,比我家泥夯的房子气派多了。“聋伯”比“大聋伯”个子高些,但“大聋伯”有一把很入画的大胡子,让我很有摸一把的冲动。他们说话大声大气,两兄弟,一个会说书,一个会下象棋,但那时候我还小,听聋伯说《西游记》,和大聋伯下象棋,以及津津有味看蚂蚁国的《南柯太守传》,都是后来的事情啦。那时我还小呢,我整天就是玩。我和我的同年佬、金红,曾经为一只八哥送葬——八哥是我爷爷给我捉来的,被我们玩死了。我们决定挖个坑把八哥埋起来,然后学“哭娘”——哭娘这一套,在我家东边的雨台屋里——它曾经是阴司屋——是常有的事,我们耳濡目染,差不多就会了。我们为八哥选的墓地就在我家前面稍远空地。我俩还没开哭就招引了不少人围观,“生身娘啊——”、“我的爷——在世做侬好——”,我们把他们都哭笑了。
我家门口空地,除了摊地簟晒东西,经常会“焐火泥灰”——有时是我家,有时是益基家,有时是文明家,反正这个大院基是大家共用的。“焐火泥灰”就是把各种杂物,比如各种草连同草泥、碎豆叶、豆壳、花生壳以及晒得半干的花生叶、甘蔗渣以及其它勒色,经过火焐之后,做成有机钾肥,用它给番薯施肥、用它种油菜。焐的过程比较长,一般是傍晚的时候堆成堆,点火之后,变成暗火,焐着,第二天早上那个就成了火泥灰,还是温的,有时候还有明火。在夏天的夜晚,有人还利用这火泥灰,用晒干的艾草熏蚊子,在空地上睡竹床过夜。有一天早上,我起来,大人们都出门干活了,我对付掉早五更的粥,有些百无聊赖,出门左侧就看到了一堆大大的“火泥灰”,我就用根棍子拨弄,嗨,还真有火星。于是我返身回家,拿了几个毛芋,去煨它们。我把毛芋埋入火泥灰,还顺手把一个朽烂的小树桩也扔了进去——这个树桩是爷爷从溪滩里捡回来的,溪滩的杨柳树林里,经常有这样的树桩。
隔一段时间,我跑过去看毛芋,结果在裸露的树桩上看到密密麻麻的“虎娃”——在火泥灰外侧的树桩上虎娃们奔跑、蠕动、翻滚,有一些已经烤焦,有一部分聚集在地面,但更多的虎娃依然拥堵在这个小小的树桩上,这让我惊讶莫名。我赶紧把这个冒烟的树桩勾出“火泥灰”,轰一下,我看到了更多的虎娃,树桩冒烟的一侧已经烧红,这些散乱的虎娃并未四处逃散,它们依然围拢过来,围着这烧红的树桩跑,有些居然不管不顾跑到了火星里,噼里啪啦,焦臭味更加浓郁了。我蹲着看了好久,因为烟熏,我不停地眨巴眼睛,然后我反身折回,舀了一瓢水,跑一路洒一路,往下浇水时,我尽可能地控制好水线,瞄着烟火的那一端淋下去。在嗤嗤的烟雾升腾中,我看见蚂蚁四散,稍后,它们又一次聚拢,依旧围着这“水深火热”的树桩很茫然而焦灼地跑动……
很多年之后,我明白这个烟雾腾腾的树桩某处,是这些虎娃的巢穴,它们依恋不舍不愿离开的是它们自己的家。很多年之后,我的爷爷、父亲和母亲依次辞世,我家泥夯的老房子人去楼空,但这又破又旧的老房子依旧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回望。
虎娃,虎娃——
千张豆腐买来罢,
酒肉你自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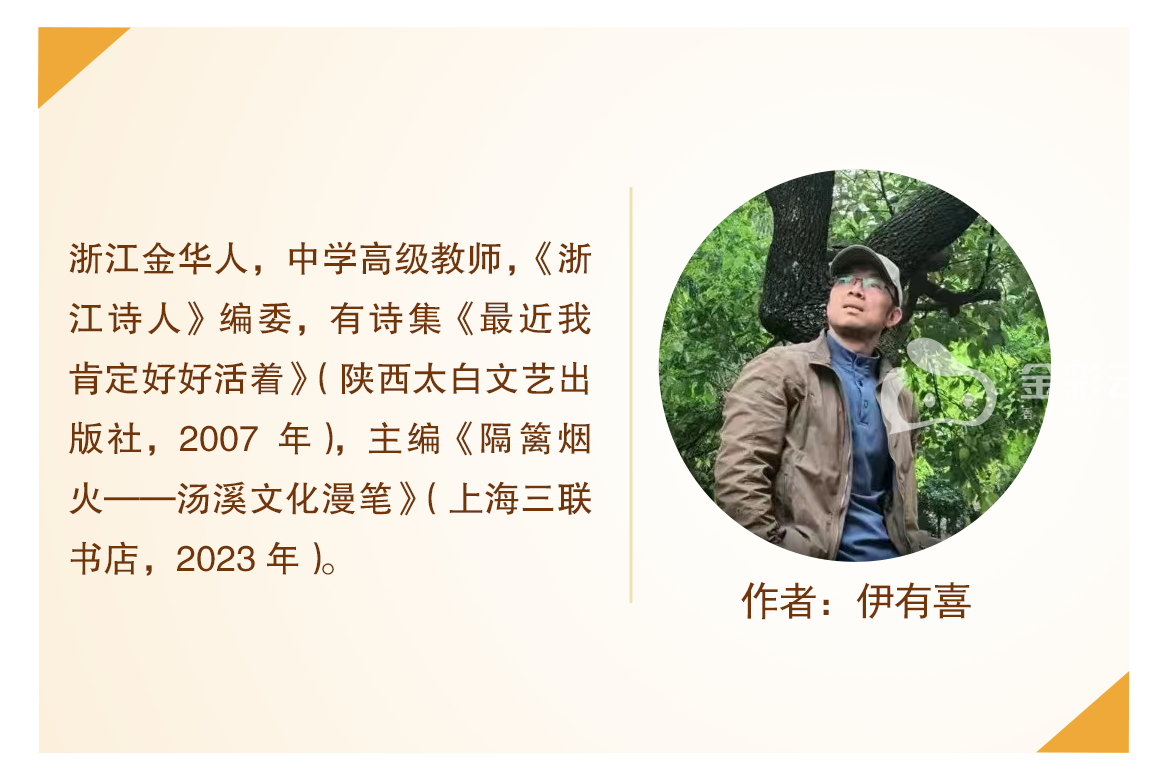








精彩评论( 0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