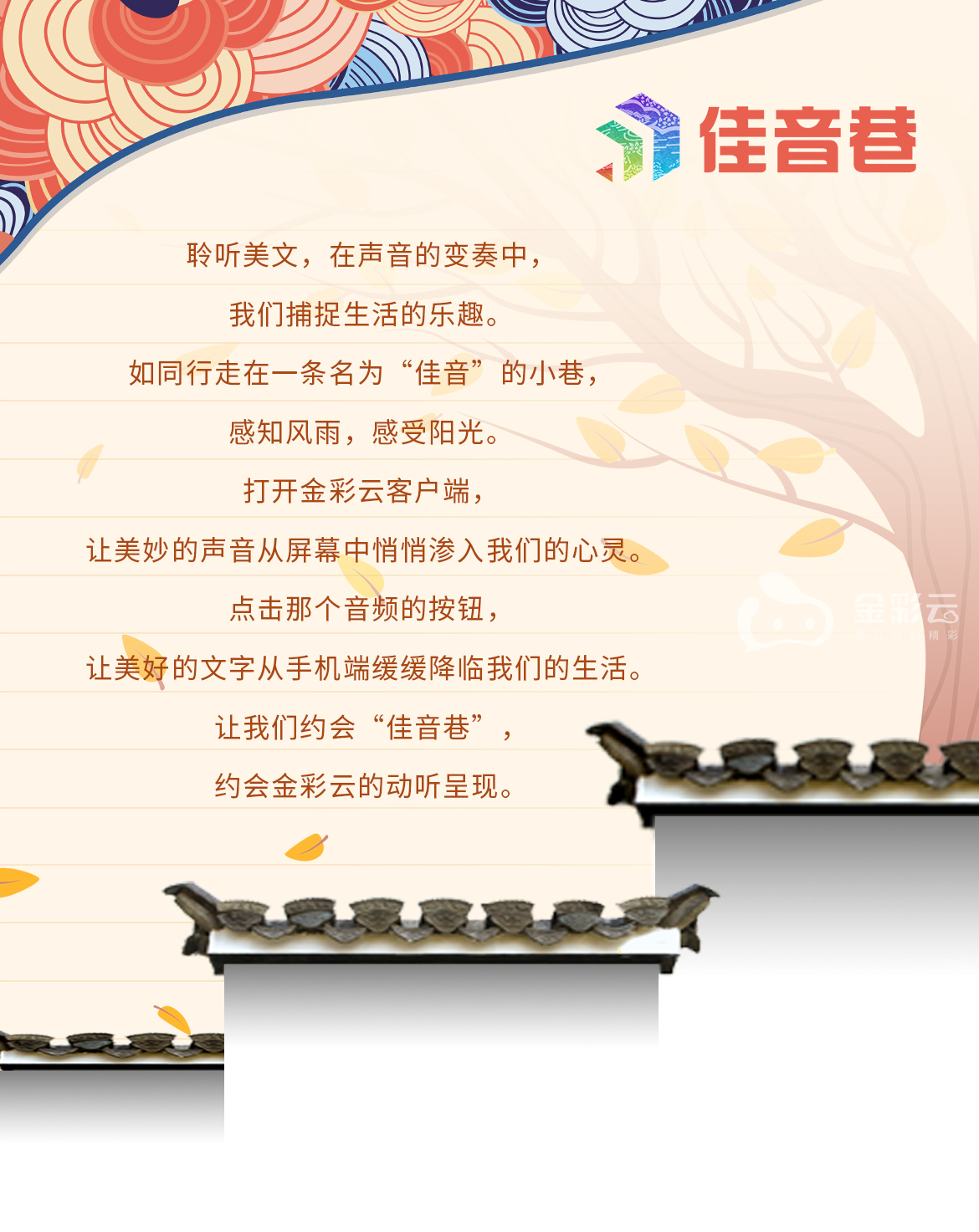
蓼花醉清秋
作者:金慧敏 朗读者:王益民
(点击音频,一起聆听)
“燕子矶头红蓼月,乌衣巷口绿杨烟。”站在南京的燕子矶头,没看到长江边的红蓼,倒是忆起了纳兰词中这一句,脑中自然就有了燕子矶边,月从江中缓缓升起,江边红蓼成片的画面,美得不可一世。或者,纳兰想说的其实只是色若红蓼的月亮,而“红蓼月”这样美的词也只有如纳兰般的人才想得出。
一场秋雨,夜又凉了几分,雨后的天空干干净净,一轮圆月悬挂半天。我忽然想起“红蓼月”这个词来,这个时候想必家乡的蓼花正开得娇艳妖娆吧?

夏花十册荷花红蓼图 清 董诰
红蓼有一种是辣的,一种不辣,我老家的人不管辣与不辣,一概叫做辣蓼。红蓼几乎是沟沟渠渠里随处可见的植物,墙角、坡地,甚至在阴沟里也会顾自长出几株来。秋天时,漫波、漫沟、漫滩头的红蓼都顶着狗尾巴一样的花,玲玲珑珑,开成一片。花小小的,不管是白粉色还是梅红色,都不如桃花的媚,也不似菊花的灿烂,甚至连梨花杏花都不如,更别与梅花相提并论。因生长环境的别无选择,更有些轻贱的意思,谁在乎那随处生长的花儿,更何况那序状的花是米粒样、绿豆般的小。但是如果你有心,细看时,那花还是挺好看的。白色的花瓣,白中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粉色,如少女的粉面桃腮,梅红的,梅红里包着蔷薇白,却又有了成熟女子的妩媚。
小小懵懂的年纪,总记得秋天时,二叔婆会把自己织的白土布用蜡画出花鸟虫鱼的样子,然后用一种草叶和石灰染出一块块靛蓝的花布。那时,但凡居家精细过日子的农妇们都会做这种活,只是平常人家染的花布看起来更拙朴些,花与底青白分明。也许是偷懒吧,只管是画了花,一次一次反复地染、晒,把一块块布料从浅蓝染到深蓝就算完事。二叔婆不然,她总会在染的过程中,把那些花鸟虫鱼根据需要再描一次花,再染,如此多次。当除蜡洗净晾干后,那布上的花花草草就有了深浅不同的颜色,倍显生动、好看。我好奇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叶子,可以染出这种神奇的颜色。二叔婆就笑着指指天井阴沟里长出的几株辣蓼:“呶,就这种。”
原来就是这种随处可见的东西啊!我和小伙伴们心领神会。有一天,打完了猪草的我们,割了一大竹篮的辣蓼,抬到二叔婆跟前:“二叔婆,给你染布。”站在桂花树下的二叔婆看着一个个脸上脏兮兮,眼中兀自泪水不干的我们,笑得花枝乱颤,脑后的发髻似乎也在秋风中颤巍巍地抖动着。我们不解地看着二叔婆,为割这一大篮的辣蓼,我们个个都被辣得流了不少的眼泪。二叔婆只管笑,笑得流出了眼泪,我们终于恼了,把辣蓼堆在天井,一个个都悻悻离开了。好像自那以后,我再没去看过二叔婆染布。
后来我们都上学了,那种青底白花的布却处处陪伴我们生活,那种布,用得最多的当是桌布、围裙和被面。这种家织土布,染了色后做成被子,翻进棉絮,特别的暖和,只是那土布上的靛蓝像是少年时代一个沉沉的梦,总也醒不过来。走亲访友留宿时几乎都是盖着这种被子,透着乡下人过日子的踏实和纯朴的本性。再后来,那种土布渐渐被花洋布取代了,花洋布的触感更细腻些,但我私下总觉得盖花洋布被子的冬夜似乎更冷一些,盖着蓝土布被子时做的梦更真实一些。可是在那个花洋布取代蓝土布的时期,乡下人家,如果谁家还盖着这种蓝土布被子,面上总会闪过一丝惭愧的神色。在漂亮的花洋布面前,那种蓝印花土布被子在人们的眼里暗暗褪了色。后来,花洋布也渐被丝绸被面替代了,再后来,丝绸被面也被各式各样更好看、更大方的整套床上用品给取代了。
我是长大后读到《诗经》里的“终朝采蓝,不盈一襜,五日为期,六日不詹”才知道,那种可以用来染布的草叶植物叫蓼蓝,跟红蓼同属,诗经中“山有乔松,隰有游龙”中的“游龙”才是我们所熟悉的红蓼。走在苏州古朴的小巷子,在博物馆橱窗中看到一件用蓼蓝草染的丝绸衣服,如青烟笼月,梦幻般的美丽,原来蓝草用来染丝绸,染出来的竟是这种韵味啊!我只道蓝草粗拙,我以为蓝草只适合那种平民化的土布,只知道那是种民间烟火般朴实温暖的颜色,却原来同一种染料,用不一样的布料,竟可以赋予它如此高贵美丽的气质。或许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,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解读。
然而,不管是红蓼也好,蓼蓝也罢,都开着差不多的序状小花,此时,都应该开遍了山坡沟渠滩头吧?陆游有《蓼花》诗:“老作渔翁犹喜事,数枝红蓼醉清秋。”不由让人觉得,因有了这蓼花的加入,也因了那蓝色的洇染,秋天更添了一些草色的诗意和韵味。










精彩评论( 0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