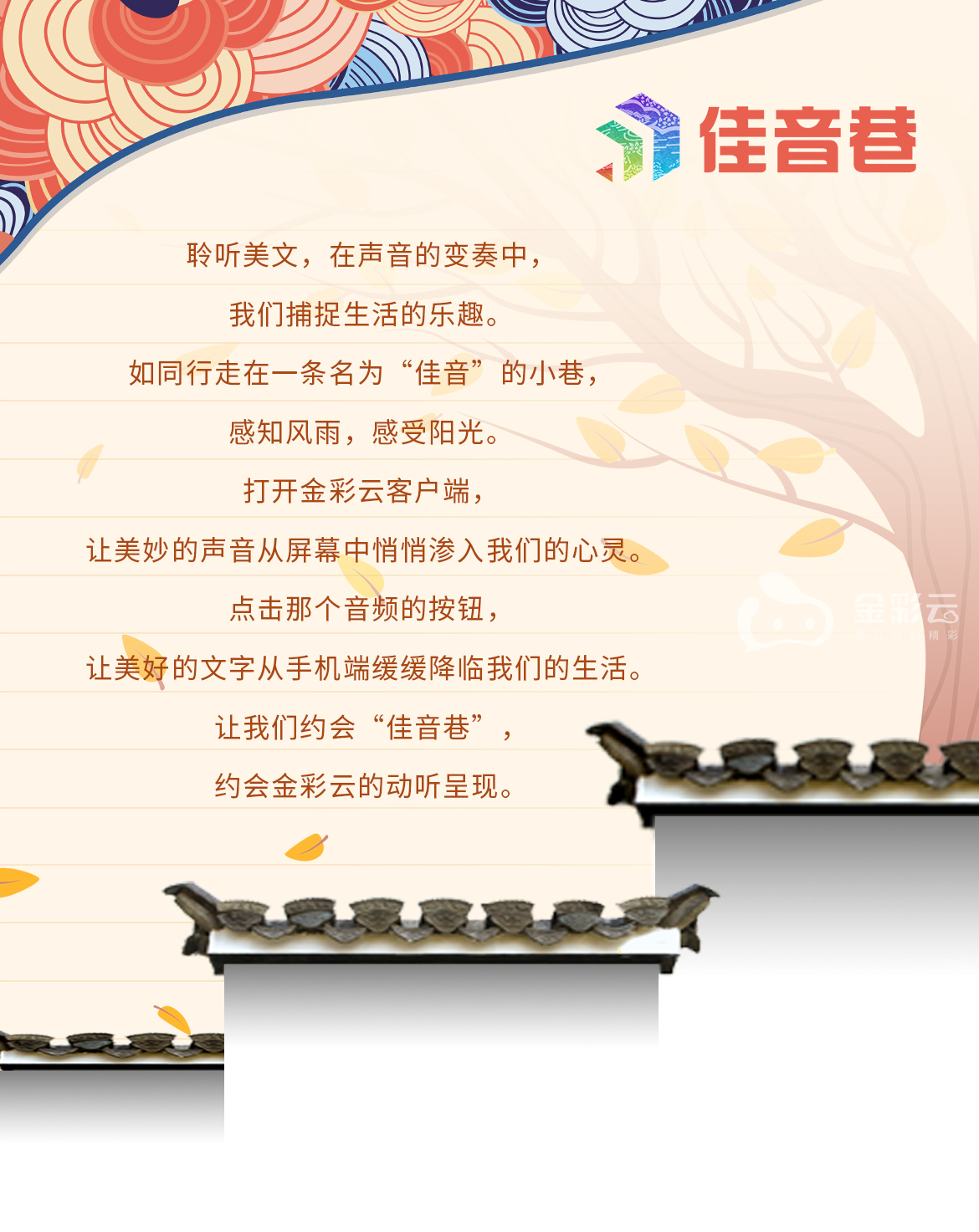
马塘村·宋代古茶场
作者:胡海燕 朗读者:胡英杰
哪有什么古老的东西。他这样说道。
他是和我们一样慕名而来的游客,已过知天命的年纪,看待事物有了自己的判断。又踢踢倒塌在一角的石柱,石柱已不完整,破碎,断裂,即便堆在一处,亦是貌合神离。这样的破碎给人老态龙钟之感,仿佛它们都是从遥远的时间深处赶来,赶累了才成这般模样。浑身又落满苔藓,愈发添了古意。
我指了指石柱,意思是这总应该有年头了吧。
他摇摇头说,也老不到哪里去。语气中带有一丝惋惜,还有一丝不屑。
到了古茶场,探寻古意似乎成了主要目的。四下搜寻的是哪个物件上了年纪,岁月痕迹明显,若是发现年岁久远的,便如获珍宝,即便它亦是只能远观不可亵玩,只能处在原来的位置供人怀想,但那样的怀想早已穿透时间的城墙,有了厚度和纵深感。也会将此物与他物做番比较,谁更老,谁更有价值,仿佛是道数学证明题,要用一种古老去求证另一种古老。这是观众的势利,非要趋附在本无半点城府的事物上。
而它们各顾各的,任凭时间一刻不停磨损它们,消耗它们。墙倒了重新砌回,屋顶漏了加个瓦片,门板坏了重新装上,而有的牛腿、雕栏、画栋残缺了就让它残缺着吧,残缺也是一种美。它们活得比我们通透。新的如何,老的又如何,都只是万千世界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,时间的洪流会抹平它们,淹没它们。即便机缘巧合,时间将它们拱手奉出,仍会以我们不可知的方式消失不见。这世上有太多事物就是这样来的,又是这样去的。它们的存在或许真能说明一些事情,让人类有机会顺着时间的绳索追溯而上,直至遥远的源头。但很多时候,事物只是事物,是我们丰富的情感以及想象力丰富了它们的过往而已。
如此,古茶场只是古茶场,仅仅是时间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而已。它的价值,也许在于让我们透过留存的老物看见了虚无的时间,唐朝的,宋朝的,清代的,民国的,这些原本抽象到迷离的朝代有了眼目可及的具体呈现。
相传,早在晋代,许逊周游各处传播道教,游历至此地,见茶树满山遍野,质量上乘,但茶叶滞销,农民生活清苦。于是,许逊就在此地留了下来,与茶农一道研究加工工艺,制成“婺州东白”,并派出道童到各庙庵施茶,受到各方好评。从此,“婺州东白”畅销各地,到唐代,“婺州东白”被朝廷列为贡品,并被收入陆羽的《茶经》中。到宋代,皇室定都临安,茶场成为“榷茶”之地,朝廷委派官吏进行交易管理。于是,茶场成了浙中茶叶交易中心。
遇见许逊是老百姓的幸运。许逊追崇的虽是修道成仙之事,关心的却是民生疾苦。也许他在潜心研制“婺州东白”之时,属于他的“道”已悄然而至。后来,当地茶农奉他为“茶神”,尊称他为“真君大帝”,顶礼膜拜,千百年来从不间断。
从古茶场西面的门口进入,目光与茶神相遇,他慈眉善目,笑意盈盈。一旁测字算命的阿公说:拜一拜,很灵的。阿公是本地人,操一口地道的玉山方言,八十多岁仍耳聪目明,亦有几分仙风道骨之气,不知是否与日日守着茶神有关。在阿公心里,茶神是一个“很灵的”神。
其实,在当地茶农心里,许逊也是一个“很灵的”神。他们质朴而虔诚,用古老的礼仪表达自己的崇拜。每年春茶开摘,茶农便奉上第一株新茶,先祭“茶神”。秋收后,茶农又来拜谢“茶神”。于是,两次盛大的庙会“春社”和“秋社”应势而生。正月十五举行“春社”,祭茶神,演社戏,挂灯笼,迎龙灯。十月十六举行“秋社”,祭茶神,迎大旗,演社戏。我参加过“春社”和“秋社”,那是万人参与的盛会,热闹和排场令人赞叹。《玉山竹枝诗》云:“茶场山下春昼晴,茶场庙外春草生,游人杂众香成市,不住蓬蓬社鼓声。”而这样的盛会,是乡人自发组织和参与的,他们想用这份热情表达真诚的感激。这份感激穿越了漫长的时间,穿越了人神之间的隔离,如此富有仪式感,如此熨贴人心。
许逊是古茶场最古老的神,是茶农最信任的神。
茶博馆内的三块石碑被称为“镇馆之宝”。清代道光年间,朝廷在茶场立“奉谕禁茶叶洋价称头碑”,咸丰年间立“奉谕禁白术洋价称头碑”,光绪年间又立 “奉谕禁粮食洋价称头碑”。三个不同时期,官方在此设立关于茶叶、药材、粮食的称头碑,现在集中展示于一处。如果一块称头碑代表着一个时间,那么,仿佛是将三个时间压缩,而后肩并肩地站在一起。石碑上记录着价格和交易制度,文字已模糊,即便在强烈的灯光下亦是不可明辨,似乎是被哪只大手悄悄抹去,留下依稀的身影。
但不管模糊与否,都说明着在古代,茶场于官方于民间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实用价值。而有幸如能此完整地留存下来的,即便放眼全国亦是寥寥无几。据说,古茶场的存在填补了我国文保史上的茶文化空白,被列为全国文保单位。
下雨了。古茶场只剩下我们,变得空旷。静极了,如丝如缕的细雨斜织着,润物无声。置身于这样的静中,仿佛看见时间针脚在走动,一会儿拉得很远,一会儿又拉得很近。
想起一个人的诗:
我们心里是否仍有空地,放得下一个茶桌
万事沸腾,终究半凉
这无边空蒙,正好收进一盏茶里
世事也许真如一盏茶,不管曾经辉煌如何,终究归于沉寂。但这份恬淡的心境,仿若茶场的无边空蒙,需要走过人生的千山万水方能明白。
也坐下来喝个茶,喝一杯“婺州东白”,在袅袅茶香中体味来自玉山山野大地的清欢。或学一学唐人煮茶,“采之,蒸之,捣之,拍之,焙之,穿之,封之”,而后用火烤炙,用茶碾碾碎,用筛子筛成细末,再放到开水中去煮。又或学宋人点茶,炙茶、碾罗、烘盏、候汤、击拂、烹试,一步步不慌不忙地走下去,将时间和心思一点点收笼起来,慢条斯理地喝出茶之雅意。“无由持一碗,寄与爱茶人。”我们虽不如他们讲究,用大盖碗、玻璃杯冲泡出的“婺州东白”或许过于直白,但“婺州东白”还是“婺州东白”,就如不管风云如何变幻,茶场还是那个茶场。若是没有茶,就这样坐在廊檐下也好,思绪里关于茶的故事风生水起,正穿越浩浩汤汤的时间山水奔赴而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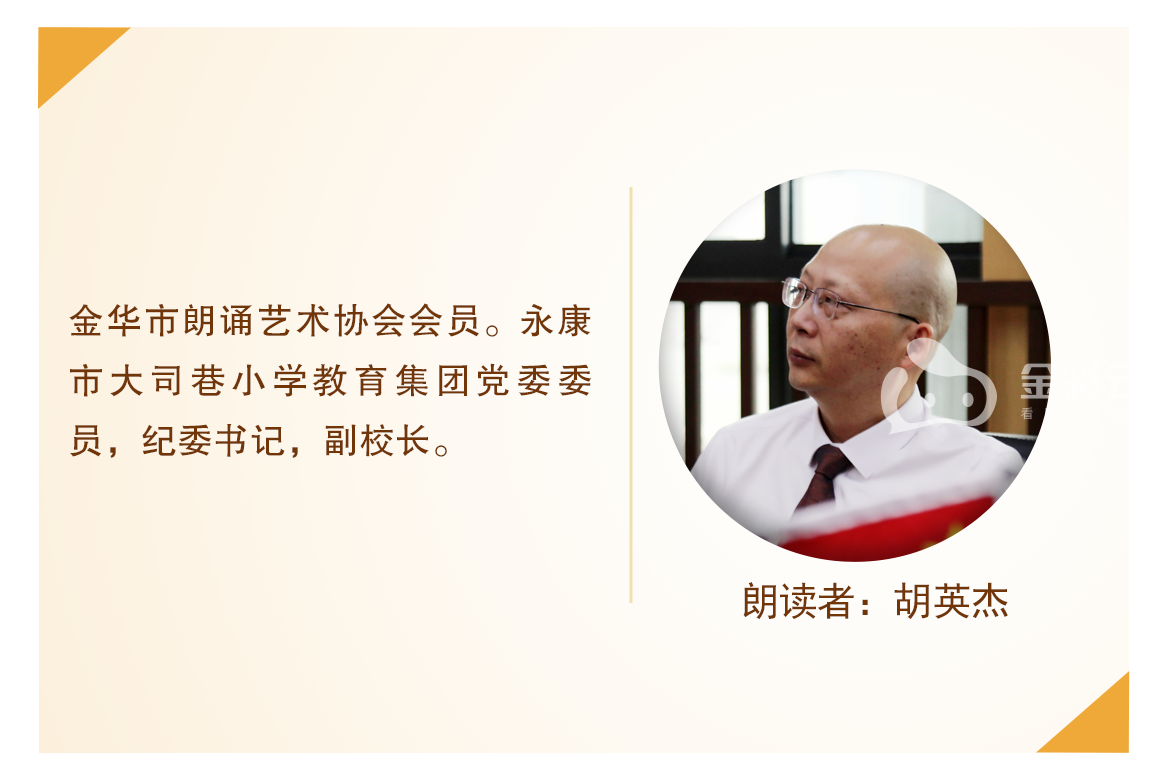






精彩评论( 0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