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▲点击音频,一起聆听▲

作者:杨 荻
诵读:姜 维
1974年我在瓜洲小学上学。学校是村口的小祠堂改建的,几间平房充当教室以及老师的宿舍,老师有村里姓王的女老师和来自杨砩头的杨美力。杨老师很偏爱我,他师范毕业,是那个年代的时尚青年,相貌英俊,热爱运动,为人热情又稳重,说是我的偶像也不为过。
学校敲打一截废钢当作上课钟声,当当当的清脆声响每日传遍村野。学校与我家只有百来米,隔着一丘稻田,听到钟声,我跑过田埂去上课。

我的读书成绩不错,年年评为三好学生。记忆中,天色暗沉的大雪天,我踩着高跷去学校领奖状,内心骄傲。
大概三年级的时候,村里在溪滩上划出一片沙地给学校,种麦子、豌豆等蔬菜,上劳动课,学生们去松土、除草、割麦、种菜、施肥。后来,学校又养了四五只羊,下午放学后,学生轮流去放羊。我从未放过羊,拿一根竹竿赶到山坳的青草坡上,任它们自由吃草,自己往地上一躺,目光从这个山头漂移到那个山头,看风推着白云赶路,不知道这些云在哪里宿夜。
那时我感到阅读的饥渴,家里没有什么书籍,只有一本《赤脚医生大全》。父亲有时会从山里学校带回来几张《参考消息》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,我读过一个叫《于无声处》的剧本,不太懂,其它的更不好看。过年时,我在外婆家看过《水浒传》几个章节,是表弟华云带来的书,令人废寝忘食。
我还没有去过县城。它在西面,日头落下的地方,听人们说,过了瓜洲渡,还要翻好几道岭。
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羊已跑进庄稼地,听到坡下传来村民愤怒的叱骂,才慌忙跑下去。羊好动,不像牛那么老实。

日薄西山,好不容易把羊赶回学校,当过羊倌的同学前来验收,说羊还没有吃饱呢,肚子瘪瘪的。我就去溪滩割一捆青草扔进羊圈里。
羊养了一年多,后来宰杀了。我忘了有没有喝到羊汤。
不放羊,却要放牛了!生产队派人去白水洋买一头水牛,买牛的社员趁机胡吃海喝,醉倒路上,牛也跑了,好不容易才寻回来。队里20多户人家轮流放牛,一次三天。不上课,我便替母亲去放牧。
遇到下雨天,我穿上不合身的蓑衣,戴上笠帽,牵着牛去山野。“牛得自由骑,春风细雨飞。青山青草里,一笛一蓑衣。”“东风放牧出长坡,谁识阿童乐趣多。”我后来读到描写牧童的古诗,哑然失笑,放牛哪有这么多诗意!真是“有我之境,以我观物,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”。要知道,大雨滂沱,我得躲到灰庐里;乍暖还寒,我冷得瑟瑟发抖;牛踏了人家的麦子,别人要上门告状;夏日,山里的蚊子多得像一团飘忽的黑雾。
即使丽日晴天,我还要割一捆牛草,或者捡一捆柴。牛喜食苜宿草、狗尾草、黑麦草、一年蓬,但我割得最多的是芒草,因为家乡的土地上,它最丰茂。芒草边缘有密密的锯齿,极易伤手,牛却不怕。水牛吃草时先用舌头撩卷,再用牙齿撕扯,然后是一磨一合地咀嚼。我有时候把手伸到它嘴边,让它温湿的舌头舔舐,一下一下,痒痒的。

水牛性情温驯,但犟脾气上来的时候,四脚像钉在地上,弯着牛头,任你怎么拉都纹丝不动。
我当然要骑一下牛,个子太小,牛的肚子像一个大包,攀不上去,我把牛停在山路上,人爬到地磡,借助高差跨上去。虽然牛的脊骨一步一滑把我硌得生疼,但我志得意满,像古代得胜回朝的将军。乐极生悲,山路很陡峭,牛身倾斜得很厉害,它猛一低头,我骨碌碌从牛角之间翻滚出去,当场摔晕在路边。大伯正在山地拾掇,见状叹口气,将我背回家去。
牛就被拴在祠堂后面的山麓牛棚里。一丈见方的泥墙棚屋,地上满是污泥,木梁上搁着几捆干稻草和玉米秸——那是入冬后的食物,四面漏风飘雨。一方杂木钉起的栅栏掩上后,牛绳绕一绕就行了。
春耕时节,牛满负荷劳作,除下牛轭,牛颈都皲裂了,结一层盐霜,身上的鞭痕也多。把它关回牛棚,成群的蚊蝇“轰”地落在它身上,吮吸它的血,它身上的几处伤痕已经结痂,有些又裂开了。胡桃大的纯净牛眼,多了忧伤和呆滞,我深深同情它,抚摸它的头,却无力改变它的处境。

那一年秋天,它不小心踩空了道路,跌下高高的田坎,把一条腿摔断了。一条断腿的牛又有何用呢?牛被杀掉前流下了滚滚的泪水,我觉得它是短暂地回顾了一生,但是它没有哀鸣,沉默如同往常。那是社员们狂欢的日子,祠堂的蚕房里非常热闹,雾气蒸腾,人人大呼小叫,步履生风。每家每户都分到几斤生牛肉,剩下的搁在两口硕大无比的、用来煮茧的大镬里,煮了吃肉喝酒。人们兴高采烈地围着铁锅,闻着香气,等待牛肉烂熟,不断咽着口水。
母亲做了一碗红烧牛肉,嘱我送往双庙的外婆家。我满头大汗走到新路村时,一个肮脏的老头问,小孩,篾篮提的什么?我说牛肉。他贪婪地吸吸鼻子。
后来,我听说牛皮和牛骨也卖给货郎担了。一头曾经健壮无比的牛,只剩下一副在异乡漂泊的骸骨。
我的牧童生涯也戛然而止。
1979年,我稀里糊涂地考上下各中学,父母很开心。那一年,学校在下各、朱溪两区招收两个特招班,初中高中连读,学生一律住校。
我挑着木箱和草席铺盖来到10多里远的怀仁,内心怯生生的,像一头走失人间的小兽。
这里是公社和区政府所在地,有丝厂、铁钉站、机械配件厂、汽车站、饭馆、书店,甚至还有电影院。
眼前的陌生世界变得宽广,而生养我的血地渐渐远去了。
我不知道前路是什么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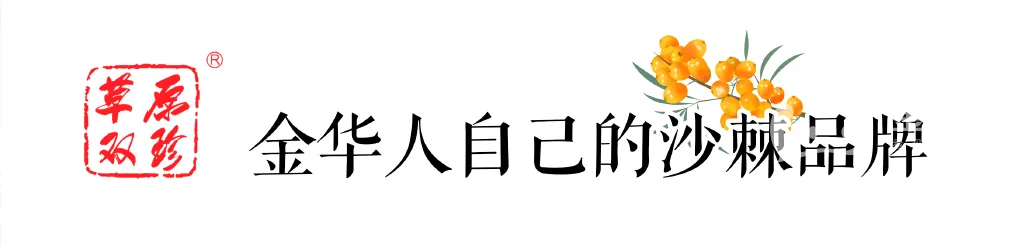





精彩评论( 0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