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
作者:潘江涛
诵读:楼华坚
在某个山村,谁家杀鸡也许无人知晓,但黄昏时刻,铁锅里飘出的阵阵浓香一旦弥漫村庄,这户人家便成了人们猜想的中心:是家中来了客人,还是家人久病初愈?
美食既诱人食欲,也让人暗生妒忌。我贪婪地吮吸着鸡肉的香味,幻想着有一天一个人吃它数十只。
日子像流水,如今面对满桌子的鸡鸭鱼肉,我已兴味索然。
不过,每每说起村子里那只仍然散发着浓郁香味的鸡,除了自己依然一往情深之外,同餐之人往往一笑而过。
这也难怪,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鸡,更不知晓是怎样料理的。甚至会说,留在我味觉深处久久不去的“好吃”,兴许还是自己嘴馋的缘故呢!
鸡虽是寻常的家禽,但“鸡功最巨,诸菜赖之”( 袁枚·《随园食单》),吃法数不胜数。且不论取鸡的各部位入肴馔,单就整只鸡的吃法,就不下几十种,像“黄金鸡”“贵妃鸡”“太爷鸡”“荣华鸡”“叫化鸡”等等,足见中国烹饪之精深。然而,最难忘的,还是老家磐安的瓦罐煨鸡。

瓦罐煨鸡颇有讲究。瓦罐不能取宜兴紫砂、陶瓷一类的泥坯,必须是本地黏土捏成、土窑烧制,多为敞口,褐黑色,不上釉。鸡为家养土鸡,即城里人所谓的本鸡,不食饲料,专吃青草、虫类和原粮。
土鸡个头不大,但肉质细韧,翅膀、脚掌瘦而细长,一看就是觅食飞捕的老手。
宰杀洗净,斩块放入瓦罐内,不加水,也不加酱油一类佐料,除生姜外一律免除。一公斤鸡加等量的家酿米酒。
别以为如此这般就可以煨制了。在煤饼炉出现以前,瓦罐煨鸡通常要用灶头的大饭镬。
先在镬底垫放四小块破瓦片,把瓦罐平稳地置放在瓦片上,再在大饭镬上倒扣一个小铁锅,大小铁锅之间用炉灰密封。最佳燃材是稻草和秸秆,六七捆,烧上两三个小时左右,保持火苗不断。
当然,这是最原始的煨制。如今,即便是农村,不要说稻草和秸杆难寻,就是一个人守着灶头两三个小时不离不弃也不容易。因此,简易的煨制方法是将大饭镬置放在煤饼炉上,其它步骤不变。煤饼炉替代老柴灶是瓦罐煨鸡的一大进步,既省时又省力。
瓦罐煨鸡是极富创意的构想——不煮、不蒸,也不是干烤,硬是靠两口铁锅中的温度烘烤,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鸡的原味,使鸡的鲜香不受损失,加上间接加热,时间又长,从而形成了它色泽金黄闪亮,油而不腻的特点。也许,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火,终是吃遍南北,也是绝无仅有的。
瓦罐煨鸡的最大特点是“香”,一只鸡香透一个村,故有“百步香”之誉。揭去倒扣铁锅,顿时异香扑鼻。捞一块尝尝,鸡肉不老不嫩,口感极佳。味道始是清淡,渐渐味愈浓,余香在唇在舌,在空气中,久久不散。那“汤”原本是家酿米酒,因为融合了鲜美鸡汁,便显得更加醇厚。
有一次,省里一批作家去磐安山乡采风,连吃了两煲“瓦罐煨鸡”,还不过瘾,又每人要了一只黑不溜秋的瓦罐。那样子,真把瓦罐当成了宝贝。殊不知,没有家养土鸡,再好的瓦罐也煨不出“百步香”来。
年少嘴馋,老是惦记瓦罐煨鸡。但在“玉米面当细粮,鸡屁股是银行”的年代,那只大公鸡是父亲起床耕作的报时钟,那几只老母鸡是母亲换购油盐酱醋的财源,只只都舍不得宰杀,一年到头也就难得吃上一顿“百步香”,除非父亲大病初愈,急需滋补。因此,美美地吃一顿“百步香”,也就成了童年之奢望。
瓦罐土鸡好吃喷香。只不过,开放搞活之后,村村落落都搞“市场化”,转悠于房前屋后的土鸡原本不多,哪经得起人人惦念?

于是,头脑活络的经济人,摸准回归传统的饮食潮流,包下荒山,放养本鸡——虽比不上家养地道,却练就了一身“轻功”,能像《卧虎藏龙》里的侠士一般在树林间扑腾。有了这身功夫,既能躲避天上飞的老鹰、地上跑的野兽的袭击,人要捉它也得出一身大汗。夜晚,它们寄宿在树叉间,做着高高在上的美梦。白天,它们飞落下来,除了啄食林地里的虫子、喝山涧里的泉水外,还吃特地为它们配制的中草药,其中居然有当归、太子参等。养鸡的人说,土鸡要自然滋补,而它所吃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更好地吃它。
听起来,这话颇像清代美食家袁枚的咏《鸡》诗:“养鸡纵鸡食,鸡肥乃烹之。主人计自佳,不可使鸡知。”(《随园诗话》卷七)
“鸡不能吃自家养的,鱼必须吃自己钓的。”这是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高见。他在解释这种感受时说,鸡“通人性,吃时下嘴难”。
不过,我倒觉得,所谓鸡美鱼鲜,被吃之“鸡”,最好是自己养的,至少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本鸡。而钓鱼之人吃鱼,追求的是“钓趣”,至于“鲜味”实在所求无多。
好久不吃瓦罐煨鸡了,很是念想。上个周末,相约三五好友,带上锅碗瓢盆,举家外出野炊。途经养鸡场时,趁“鸡”不备,捉住一只公鸡。宰杀洗净,垒石蒸煮——虽没有瓦罐煨制,也无米酒佐料,却有清清的山泉和新鲜的姜蒜助烹,聊胜于无,幽幽鸡香还是诱得大家馋诞欲滴。
在朗朗晴空下,大家席地而坐,既赏山水情趣,又品本鸡美味,悠哉快哉,乐赛神仙!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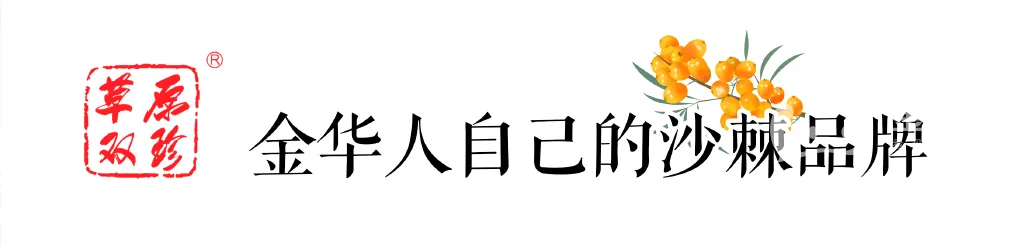





精彩评论( 0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