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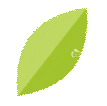
作者:程卫通
诵读:赵婉屏
屋脊瓦舍已泊在暮春的媚光里。
从东朱古村一开步,浙中义乌南部的雪峰岭古道,就是斜上的蜿蜒幽路。那天我与妻去往古道,淡云高浮,树影摇寂,是很适宜闲游的。
东朱是我的老家,我俩自结婚那年走过古道,就没有再去了。好在古道还在那里,且经多次加固修筑,不仅未荒废,还被列为国际登山健身游步道了。雪峰岭群峰簇拥,地僻山深,在我印象里是很少有人去的。拙朴清苍中的兀自寂静,应是岁月不断更迭后仍然破不了的意境。
我们想去看瀑。雪峰岭边,一挂栖隐于林壑的涧瀑。
到达岭脚的雪峰水库,贴着山腰,一道曲折缓缓向上攀伸而去。面库临水的陡坡下,不时有壮茂的老松,苍苍然托举着山风横枝展翼。细密的松针是苍劲而森绿的,驻枝偎依,临空四放,然后就毫无畏惧地刺向周遭的凡俗与风尘。我便敬畏地停步驻足,很有些耐心地多看了它们几眼。
走完一段平阔的基路,石砌的古道已开始渐次蹬高。时有山石或峭壁在路侧兀立,踏步的长砌石横露着身子嵌阶而卧,因岁月的不断磨蚀与纷踏,其色已呈油褐,阳光落照其上,便闪出些沉沉的亮来。静静地,转过一个山弯,峦峰、林麓、巨岩、野花、山涧,尽在我的远望中了。浮光也随蹬道的迂曲明暗,或隐或现。
我竟有些恍惚起来。

那时,我终于远远看到了古道左侧突然显露出的山涧。白练垂挂,泉瀑飞溅,水声滑过丛石苍苔,滑过苍老的林莽翠稍,滑到了我的耳边。我顺流上望下探,又几度被阴翳的林带与突兀的山石突然截断,视野里时断时连的山涧,只能靠不绝的水声自主链接其隐藏的纹理,从而把水泄涧瀑一整条地在脑海里勾勒绵脉起来。
山因水而美,我的闲心散意仿佛一下子得到了激活,就随瀑声继续往古道深处走。不久看到了一处清冽的小水渚,就在古道旁边。水自高处杂石间赫然潆出,几处淌流汇聚盈积,几番洄曲闹腾后,便又随光滑的岩壁撒欢而去。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:尽头难止,源头更是难溯。谁能说清这一个湓溢的潆口就是它的源头呢?它自远山的高崖而来?还是从深沉的渊域而至?它奔波的路途是遥是近?它一路都历经了哪些坎坷?
这神秘的涧瀑,让我想到了无常的人生。
我突然产生要触碰那水的念头,便小心翼翼地下往水渚。柔软浪白的涧水从我的指尖滑过,耳边是满满的快活的水声,如古筝,如长箫,如幽笛。我仰头看站于古石道上的妻,瞬间感到异常的清欢与满足。就干脆找了块水边的巨石,俯身,安坐,闭眼。闻山风飘谷,听水声落阶,自由自在地享受了那难得的林涧听瀑之乐。
在听瀑的那一刻,山谷的清寂把水声放大了。我想起生活中一些莫名的追根溯源,一些无厘头的懊恼与纠缠。顿觉,抛却一些不必要的预想和预设,内心可能会清明踏实许多。生活在更多的时候,其实更需要水一样地自我、自然、自悟、沉寂、穿越……

涧道两边是高耸的崖壁,草木葳蕤倾情覆盖,山体斜绵寂影参差。立于涧旁,仰看那些披坡的树,青峻的溟色里,似有山岚浮空,光雾梦幻般自绿翳间轻缈飘过,凹凸的林稍不意间就有了波诡的氲色。此时我牵想着刚刚垂挂的白瀑,以及那响声里盈满的果敢与豁然,就觉天地已是另一番模样了。目光在那样的苍美与高洁里久久流连,我突然觉得自己久积于内心的某些闷郁,似乎得到了些许的治愈。
近午的阳光明晃晃地照着峡谷,我抬起头,看到了正前方山壁上两块黑峻的天然巨岩,它们一左一右形如高悬的挂钟,东朱人把它们叫做“金钟岩”。这里古称“三皇殿”,却没有殿,只有一处三面垒石临道敞口的古石亭,记忆里亭内从没供奉过什么,只是供路人歇脚用。如今却新建了一座庙,里面供奉着三位大皇,这截古道因此改称“金钟三皇庙”了。我把目光落在溪涧的右前方,果然看到了赭红的庙顶与明黄色的殿墙。
我朝峡谷连喊了几声,没人回应。我断定是座空寂的峡谷山庙。
想进殿看个究竟,妻怯怯地远站着不想随行,我便收住脚。
这里刚好是三岔路口,往左上经柿树文是雪峰岭,往右拐可达义乌著名的大寒尖。看到路边堆积的建筑垃圾,我已没有了再往上走的兴趣。
顺原道返回,悬崖处遇一挑担老者,问他新庙可有人管?他答:没有人就没人了。虽离开故乡多年,但这句绕口的乡音我还是能听懂的。后又迎面遇上一挎篮村妇,不认识,我只向她点点头,她却一直到我们走了很远,还站在原地看着我们。
鸟鸣清婉,空谷传音。横卧的石阶依然是沉沉的亮,涧瀑也依然时隐时现于幽蔽的林壑。我却突然觉得,一些古朴深邈的旧时趣意,已在刻意的翻新中悄悄跌落了,也许就撒在这古旧的陡坡石级上。是原始的荒凉和寂静,还是添加的荒僻与落寞,我说不清究竟是什么。
好在,清逸的飞瀑声,已印在心底,并与我一路伴行了。







精彩评论( 0 )